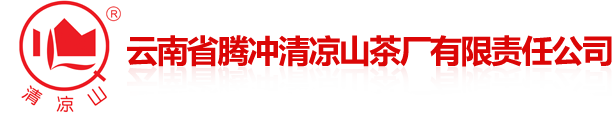討論茶文明就從"茶"字的由來開端
在古代史猜中,茶的稱號許多,但“茶”則是正名,“茶”字在中唐之前通常都寫作“荼”字。
“荼”字有一字多義的性質,表明茶葉,是其間一項。由於茶葉出產的開展,喝茶的遍及程度越來越高,茶的文字的運用頻率也越來越高,因而,民間的書寫者,為了將茶的含義表達得愈加清晰、直觀,於是,就把“荼”字減去一劃,成了如今咱們看到的“茶”字
“茶”字從“荼”中心化出來的萌發,始發於漢代,古漢印中,有些“荼”字已減去一筆,成為“茶”字之形了。
不只字形,“茶”的讀音在西漢現已建立。如如今湖南省的茶陵,西漢時曾是劉訢的領地,俗稱“荼”王城,是其時長沙國十三個屬縣之一,稱為“荼”陵縣。
在《漢書·地輿志》中, “荼” 陵的“荼”,顏師古注為: 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這個反切注音,就是如今“茶”字的讀音。從這個表象看,“茶”字讀音的建立,要早於“茶”字字形的建立。
中國地大物博,民族許多,因而在語言和文字上也是異態紛呈,對同一物,有多種稱號,對同一稱號又有多種寫法。
在古代史猜中,有關茶的稱號許多,到了中唐時,茶的音、形、義已趨於統一,後來,又因陸羽《茶經》的廣為流傳,“茶”的字形進一步得到確立,直至今日。
關于茶名茶字,我國歷史上稱謂和寫法極端雜亂。以茶名和茶字的詞目來說,不算“草中英”、“酪奴”、“草大蟲”、“不夜侯”、“離鄉草”等謔名趣名,還有荼、槚、橈、蔎、茗、荈、葭、葭萌、椒、茶、¤茶、茶荈、苦茶、苦荼、茗茶、茶茗、荈詫等等叫法和寫法。對這些茶的方言、俗稱、異體字和相互能夠通假的字,通常因其繁也就不想去探求個中的緣由。其實,若是把這些茶名茶字整理整理,找找相互間的聯系,弄不好對咱們需求搞清我國茶業和茶葉文明的來源也有聯系。上述這些茶名和茶字,看似許多,但若是咱們從音節視點大將它們一分,不過單音節和雙音節二種。若是將單音節中茶和茶義字去掉木字旁的俗寫和互可通借的橈、椒等字,剩余的,也就只要《方言》所說到的“葭”和陸羽《茶經》記載的“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這幾個字了。雙音節的除掉由二個單音節茶或茶義字構成的復合詞,如茶茗、茗茶和荈詫等等,也就只剩苦荼和葭萌二詞了。這也就是唐曾經的茶名和茶字的基本情況。那么,這八個茶葉名詞,又以何者為先呢?從現有的文獻來說,仍是以《爾雅》中關于茶的釋文為早。記載:“槚,苦荼。”
《爾雅》是秦漢間的一部辭書,“槚”和“苦荼”,也能夠說是我國漢語和漢文中以雙音節茶名來釋單音節茶字的二個茶的最早記載。關于這點,四川省林業校園林鴻榮先生在《茶事探源》一文中,考釋得十分清晰。其稱《爾雅》“槚,苦荼”的釋文,和有的訓詁書上所說:“聞雅名而不知者,知其俗斯知其雅矣”,“槚”是茶的雅名,這里是以俗稱來釋雅名。并且從晉人郭璞有關這條釋文的注釋“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這點來看,《爾雅》的編者,這里還不是以華夏而是以蜀人的俗稱來釋巴蜀茶的雅名。這里必定“苦荼”是蜀人之語。
相同,咱們上面說到的雙音節的“¤詫”,也是巴蜀的方言。這一點,司馬相如的《凡將集》中所提的“蜚廉、雚菌、荈詫、白斂”的草藥中,將茶不記作“槚”和“苦荼”而稱為“荈詫”,這顯著也是巴蜀方言的一種例子。這一點,浙江農業大學聞名農史教授游修齡先生關于我國古代作物名實考證的有關文章中講得很清晰,我國或華夏最早的作物稱號,通常都取單個音節,雙音節的名物,應思考來自國外或我國邊遠地方少量民族。所以,由上筆者不光必定我國早期文獻中的雙音節的茶名和茶義字出之巴蜀,并且適當必定,我國茶的單音節名和文,極有能夠也源于巴蜀雙音節茶名的省稱和音譯的不一樣用字。這咱們仍是以陸羽《茶經》所列的茶、槚、蔎、茗、荈這五個單音節茶名為例。眾所周知,上古無茶字,茶借作荼,唐時將荼減去一筆始有茶字。
所以,陸羽《茶經》中的茶字,咱們應還原成“荼”字去考釋。荼是茶字的前身,茶是全部茶和茶義字的“正名”,所以,茶字考源,咱們就先從荼字考證。前面說過,茶是南邊的一種樹種,喝茶和茶業初興于巴蜀,所以,我國開始運用漢語漢字的黃河流域,不光沒有茶的概念和常識,連最早記敘茶的“荼”和“槚”字,也是據巴蜀方言茶的字音,在其時的文字中選借的。如茶字前身的“荼”字,原來就具“苦菜”、“雜草”和“白色”等多種釋義;《爾雅》中提出的我國第一個指茶的“槚”字,本來指楸樹,是古代常用來做棺材和琴瑟的樹種。那么,荼字是巴蜀什么方言的音譯呢?很顯著,它是由《爾雅》“槚,苦荼”的苦荼演化而來的。
近代聞名專家王國維指出,《爾雅》中的草木魚的俗稱,“多取雅之共名,而以味別之”。這便是說,這“苦荼”的“苦”字,是指“荼”味;“荼”和“槚”,當應是共名了。對此,或許有人以為這里“荼”音讀為[tu],而“槚”讀作為[jia3],荼、槚怎樣能相共呢?其實這里的 “荼”,古不讀“徒”而讀“差[tsheai]”;槚和“差”的讀音就比擬挨近而共得來了。說清晰些,也就是“荼”字是巴蜀“苦荼”俗稱的省稱;苦荼古讀[kuatsheai],《爾雅》槚字,實踐也就是“苦荼”讀出來之音譯。
所以,我國秦漢時辭書頂用“槚”字,史籍中茶的正名又多用“荼”字,二者不光不對立,并且仍是能夠互通、互證和同源。那么,既是這樣,《爾雅》中“槚”字是呈現最早的能夠必定的茶字,后來為什么不都然后選用“槚”,如王褒《僮約》“武陽買荼”,《說文解字》“荼,苦荼也,從余聲”,《廣雅》“荊巴間采荼作餅”,在漢和兩晉的文獻中,又大多用荼字致使最終演化出來的是茶而不是與槚有關的字呢?由于其時能看到和看懂《爾雅》的,首要也僅僅少量一些儒生。另外,槚是“苦荼”的讀,荼是“苦荼”的省讀,二者沒有正確和妥貼之分,所以,全部取決于用者習氣。民間特別是大多數勞動人民,他們不知道《爾雅》的苦荼是怎樣寫的,他們寫茶,當然也就只會就省而不會去講什么讀之字了。
荼和槚字,是源之于蜀人所說的“苦荼”,那么蔎和茗、荈三字呢?蔎字的字源,比荼、槚更清晰,《方言》清晰指出:“蜀西南人謂荼曰蔎”,蔎是漢字蜀西南荼的方言的音譯。這里應該順便指出,巴蜀“苦荼”、“蔎詫”和“葭萌”等茶的方言,都是雙音節,為什么唯一蜀西南稱茶曰“蔎”是一個音節呢?其實蜀西南人稱茶,也應當是兩個音節的,這里“蔎”是漢人的音譯,很能夠是漢人在擇用什么同音字時,將雙音節組成一個音節了。所以,筆者適當必定,“蔎”不是純粹的蜀西南茶的方言,而僅僅按漢人習氣取蜀西南邊言讀的音譯。荈,孫楚《出歌》“姜、桂、荼荈出巴蜀”,晉代時,大家還指“荈”為巴蜀的方物,天然也是巴蜀的方言了。
那么,荈是不是即“荼荈”的省稱呢?這如今還正在討論中。一種定見,以為荈即“荼荈”的省稱,據《三國志》“密賜荼荈以當”,以為“荼荈”一詞,能夠也當漢曾經就存在,而荈字最早見之于三國時張揖的《雜字》:“荈,茗之別號也”;《雜字》能夠就是首將“荼荈”簡化。另一種定見,以為《雜字》從時刻上說,較《三國志·吳書·韋曜傳》還要早,故荈和荼荈這雙音節茶名無關。那么與什么巴蜀方言有關呢?與司馬相如《凡將集》中的“荈詫”有關。
“荈詫正讀為[thuantshiai],乃是巴蜀雙音節白話的漢語音譯”。茗字和荼、蔎、荈、槚的字音都不一樣,它是據巴蜀什么茶的方言而來呢?林鴻榮先生以為,它是由“葭萌”轉化而來的。關于葭萌蜀人謂茶的方言,咱們在上節現已敘述清晰。
據查,葭萌演化而來的茗字,最早見之于兩晉。如《爾雅》郭璞注稱:“今呼早采者為荼,晚取者為茗”便是。葭萌明楊慎考“萌音芒”,怎樣又能導出茗字來呢?林鴻榮以為楊慎和后來清代的一些儒生釋“萌音芒”,是誤釋,“萌”的正確讀音,因“明”。他引王力先生《同源字典》這段話證說:“清人說,古代讀‘家’如‘姑’,讀‘明’如芒等等,那也是不行精確的。假設‘家’、‘姑’徹底同音,‘明’、‘芒’徹底同音,子孫就沒有再分解為兩音的條件。咱們以為上古韻部也和中古音攝相仿,有兩呼八等。‘家’與‘姑’,‘明’與‘芒,雖同韻部,不一樣韻頭,‘家’是[keai],‘姑’是[ka];‘明’是[myang],‘芒’是[mang]。韻頭不一樣,子孫就有分解的條件了。”林鴻榮接著指出,這[keai myang],當然是古蜀人稱“葭萌”的白話。這一古蜀方言的讀音,也是后來我國史籍中四川地名“嘉明”和今日四川茶鄉一些集鎮還往往稱“嘉明”的因由。換句話說,巴蜀方言“葭萌”的“萌”,歷來就是讀明不讀“萌”。筆者擁護林鴻榮先生此說,一起也必定他所說的“茗”由蜀人方言“葭萌”而來是能夠建立的。
上面,咱們以有關史實,證明了《茶經》茶之名荼、槚、蔎、茗、荈等字,源于巴蜀上古茶的雙音節方言。實踐不只上面幾個姓名,能夠說我國歷史上全部的茶和茶義的名與字,無不都出自巴蜀方言。這一點,除巴蜀再沒有另外省能夠舉出我國史籍中的茶名茶字,是出自他們的方言了。已然我國甚至全世界的茶名茶字都源出巴蜀,巴蜀是我國和全世界茶業和茶文明的搖籃,也就不言自明了。